童年與大便
n 寫於2007年(收錄於《我們都是末日殘存者》大塊文化將於2012年9月發行)

一九九零年,我第一所就讀的小學;是全校一到六年級和所有教職員加起來只有八十幾人的小學校,校區則是把台北縣石碇鄉與深坑鄉之間的小山丘砍掉一半而建成的,我當時常因為感到樹根還留在地表下,而覺得非常不自在,就像走進移碑不移墓的舊陵寢一樣不自在。
校門口有一棵作為標的物的大樹,那棵樹因為在數年前的一場大雨中被雷劈成一半,至今卻還奇蹟似地存活著,縣政府於是把它列為保護物,並沒有因為道路需拓寬而剷除它。老師與長輩們常藉此樹勉勵小朋友:就算遇到再大的考驗還是應該堅持下去,但這棵大樹的形體非常畸形,任何一個小孩都看得出它不是自願存活下來的,每當狂風吹過時,乾枯的樹葉一片接一片掉落,也會發出窸窣的悲鳴。
「我那天晚上看到,有一個叔叔在幫樹打針,後來才知道他每天都會去打針!」
阿娟說的叔叔是鄉公所的人,我想他們是在幫大樹打類似抗生素的東西,甚至有可能是防腐藥水。但過了幾年之後,那棵大樹終究枯死了,所在的位置也變成了柏油路;而他們依然只移走地表上的枝幹,至於留在地底的樹根,也沒人在乎它是死是活,反正沒人看得到。
我通常是走後門的小路去上學,並不是為了刻意避開那棵樹,只是單純習慣走人少的地方。有位非常照顧我的劉阿姨就在後門林間搭建的工寮內工作,她當時已經五十幾歲,是常駐學校的校工。每當我的便當被同學打翻後,她都會在小木屋內煮陽春麵給我吃。我永遠是一邊哭一邊走進樹林,在遠方就看到皮膚黝黑又滿臉皺紋的劉阿姨在對我微笑,她總是不問我為什麼哭泣,只問我要吃多少,然後把細麵條丟進燒著沸水的破鐵盆內。木屋外的陽光有時會斜射進來,參著枝葉的影子,看起來並不像正午那樣強烈。
說也奇怪,我很少在樹林以外的地方看到劉阿姨,我甚至懷疑過她是神明。
當我吃完了麵,走出樹林,再沿著後門的小徑走回教室;途中往往可以看到我那凹陷變形的鐵便當盒被遺留在路上,蓋子被打開,裡面的飯菜傾倒出來,通常是鄰居送的鹹粥或吃剩的油飯。我會跪在地上徒手把殘渣撿回飯盒中,把盒蓋蓋好,再扣上尼龍製的便當帶。這時會有微風吹來,是從後門樹林的方向吹來,因為午休時間太過安靜,所以能清楚聽到乾枯樹葉掉落的窸窣聲。
我是全校唯一的『外省人』,同學們往我臉上潑水時,也會一邊笑一邊叫:「幹你娘!中國豬!」
可惜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,當然我感受得到別人的不友善,只是還不太能體會省籍情結這種複雜的東西。
常常欺負我的同學裡有一個叫阿娟的女生,她只是慈惠的小跟班。慈惠是班上的大姊大,在掃除時間都會拿水桶對著我潑灑,而阿娟是個皮膚很黑又很壯的女生,操著嚴重的台灣國語口音。我之所以對她印象這麼深刻,是因為三年級時的某一天早晨。那個早晨,阿娟邊哭邊走進教室內,扁塌的鼻頭上沾滿濕滑的淚液,人中到上唇間還粘著一大片黃鼻涕,而她哭得相當淒厲,一張大餅臉全變了形。阿娟用閩南語所敘述的經過我是一個字都聽不懂,但我看到她把上衣撩起時腹部一大片淤青、潰爛、血漬揉糊地一大坨,約有餐盤寬度的傷口表皮還不斷滲出血水,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噁心的傷口,浮在其上的組織液濕潤得像鼻涕一樣滑動。我坐在遠方望著小朋友們圍繞她驚叫,也聽見老師狂奔進教室的聲音,之後她被帶去醫院,老師也才跟其他孩子說明阿娟受傷的原因。
阿娟的家庭成員有爸爸、媽媽,阿公,阿嬤跟一個姊姊;因為媽媽沒有生出男丁的關係,造成父親天天喝得爛醉回家毆打妻女,這對當時極度重男輕女的鄉下社會來說並沒有人會覺得意外。
「阿娟的媽媽早上煮了一盤水餃給剛回家的爸爸吃,水餃放在桌上,熱騰騰的,阿娟肚子很餓所以隨手拿了一顆水餃丟進嘴裡,好死不死剛好被酒醉的爸爸看到,於是被爸爸抓起了頭髮往牆上摔…然後又因為媽媽跟姊姊出面制止,爸爸火氣更大,索性把她對著桌角用力一踹…」
老師還說,後來那盤水餃也從桌上翻倒,瓷盤破碎散了一地。
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點是:阿娟還是負傷走到了學校,由此可見這場家庭暴力對她來說有多麼的司空見慣。
這事件讓我想到對我很好、常常送鹹粥給我吃的鄰居一家。有一個週末,他們住在南部的親戚北上來聚會,於是在院子烤了土窯鷄邀請我跟爸爸媽媽一同去享用。我看到他們把包裹全鷄的錫箔紙打開,拔下剛烤好的雞腿,一隻給了身為客人的我,另一隻則給了他們家裡唯一的小孫子,然後再剝下鷄翅、鷄胸肉盛盤。大家就圍在一張大圓桌上,和樂融融,但一直到吃完我都覺得很納悶,那些年紀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們到哪裡去了?只見此時她們的父親將她們喚來,看也不看地把剩下的鷄架子、塞在鷄肚子裡提味的藥渣遞給她們,並揮了揮手指示她們離開,四五個女孩興高采烈地捧了一堆骨頭坐到遠方地上開始分食。
在他們的家規中,女孩與沒生出男丁的媳婦是沒資格上桌吃飯的。記得當時我父母也被此文化差異震驚,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後來,阿娟在小學四年級前就轉學了,據說是因她媽媽終於生出了一個弟弟,於是她們全家搬到台北市,過著幸福的生活,阿娟跟姊姊也都得到祖父母給予的豐厚零用錢。
我們班上還有另一個阿娟,是一個留著豬哥亮髮型;皮膚黑到像原住民一樣的瘦小女生。她會打赤腳走路來上學,也常被老師處罰在脖子掛上『我不說台語』字樣的板子,她只是一直哭,也不知道該怎麼辯駁,因為在我的印象之中,她真的不太會說國語。她是一個單純樂天的女孩,下課時間總會去後山抓個一兩隻甲蟲回來玩,如此她就心滿意足了。
一天早晨,已經幾近遲到時間才看見阿娟走進教室,不過當大家抬頭瞧見她的那刻全笑了出來;她的黑臉腫得跟「麵龜」一樣,雙眼完全瞇成不成形的細線…她不斷嚎啕大哭,似乎是在大喊著「好痛」。當時聽不懂台語的我只覺得狀況不對勁,阿娟的臉也已經變形到像是異形卵將孵出的前一刻;或是注入過多矽膠導致毀容的小針美容。若不是她那頭招牌的豬哥亮髮型,我還真的認不出來她是阿娟。
在一片關切與嬉鬧聲中,有同學聽出阿娟含糊的哭喊:
「阿娟說她被蜜蜂叮了啦!」
霎時氣氛變的很緊張,再也沒有人笑得出來。有三、四個同學衝出教室向老師求救,另有三、四個人攙扶住阿娟,我則是獨自站在教室的最後方,冷眼旁觀那些圍觀者的對話。
有一、兩個人對阿娟說:
「妳那ㄟ架尼衰啦?(閩南語)」
有一、兩個人露出擔心的表情:
「蜜蜂在哪裡啊?會不會追來啊?」
不過我想阿娟什麼都聽不到,在老師衝進教室的前一刻她就昏倒了。老師將完全沒有意識的她抱去保健室,過了至少20分鐘後才聽到救護車的聲音,救護車似乎是從深坑趕來的,畢竟石碇並沒有醫院。隔天校長告訴大家阿娟痊癒了的好消息,但獨力照顧她的阿嬤完全付不起醫藥費,只好由老師們代墊。說也奇怪,自從這事件發生之後,我就再也沒看過阿娟露出燦爛的笑容了。
在鄉下唸了幾年小學,也不盡然全是寂寞的度過。記憶中的玩伴有一兩個,在校外的朋友就是年紀比我稍長一點;瘦瘦高高的婷婷,只要是生日或節慶我們都會玩在一起,手拉著手轉圈圈直到兩人頭暈摔倒,然後躺在地上大笑。可惜的是她先搬去台北市住了,雖然我們身為藝人的母親偶爾會碰面,不過兩個小孩卻聚少離多,當時也沒有像網路或手機這樣方便的聯絡方式,所以慢慢斷掉了訊息。直到十幾年長大成人後才意外地在台北市某家夜店碰面,然後又過了一兩年她卻自殺過世了。
在班上還有一個好朋友叫嘉瑜,她是我們全班家裡經濟狀況最好的小孩。她的外祖父母是深坑石碇地區的地主,家裡經營茶室,表姊妹們都在自家陪酒。每當我被欺負時只有她會在一旁安慰我,我也會說故事給她聽。
某天,她告訴了我一件很特別的事情:
「妳知道張正華喜歡妳嗎?」
我身為全班最胖的女生,外號還是『歐羅肥』,實在很難想像會有男同學暗戀我。
「他每天站在教室門口時都在偷看妳喔!而且上次老師幫他擦屁股,因為有妳在場,他覺得很害羞就哭了…妳不在的時候他都不會這樣。」
張正華是一個特別的男生,皮膚黑黑的,沉默寡言,長相沒什麼特色;特別的是他出生時沒有肛門,是經過手術開刀才裝了人工肛門,以至於他沒辦法完全控制自己大便失禁的症狀。往往上課上到一半,全班同學就聞到臭味,老師又不能立即中止課程去幫他換褲子,只好讓他站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課。關於『有個滿褲子大便的人暗戀我』這件事實在無法讓我開心起來,自從嘉瑜告訴我後,我就刻意避開張正華的視線,而這個人也慢慢疏離淡忘在我的記憶中。
一天,下午三點的打掃時間,我們一如往常提著水桶及掃具去操場,艷陽斜射在黃土跑道上,映照到一坨狗屎。班上調皮的男同學用報紙墊著手掌捧起狗屎,追著大家跑來跑去,突然一個腳步不穩,那坨狗屎在半空翻騰了好幾圈,然後砸到我腳上。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奇怪或骯髒的?畢竟我家養了一百多隻流浪狗,天天都得踩著一堆狗屎才能走進家門,同學們卻圍了一圈指著我大笑,甚至笑倒在地,我只感到尷尬與無趣。
眾人嬉鬧中,突然有句話語響起:
「歐羅肥跟張正華果然好配喔!」
「大便!」「大便!」
慈惠起聲一呼,同學便此起彼落地邊笑邊喊著「大便!」,我這時才知道原來所有人都知道張正華暗戀我的事。
在同學的笑鬧聲中我瞥見獨自佇立在遠方的張正華,眼中微微泛著淚光,一語不發。
然而,我並沒有擦掉腳上的狗屎就走回教室;直接來到當天擔任清潔股長的嘉瑜面前。
「妳是不是把張正華喜歡我的事都跟全班講了?」
「……。」
「妳是不是講了嘛…」
「對不起啦…」
「…。」
她立即道歉了,我看得出她真的有悔意,但其實我本來就沒有要怪罪她的意思,我知道她可能是受到威脅利誘才說出此事,更可能只是為了得到多一點群體認同。小學生當然不了解同儕間的是非判斷,而她也完全理解自己所犯下的錯誤。
「走吧!我帶妳去一個地方!」我對她說。
「可是還要上最後一堂課啊…」
我沒等她反應過來就拉著她的手衝出教室,一直往後門的方向跑去。當時天空微微泛著橙紅色,逆光的樹林卻已一片漆黑,還有許多蚊蟲呈螺旋狀在集結飛舞,好似一條上升中的蟠龍柱。
我魯莽地撞開林間工寮門並大喊:「劉阿姨!我肚子好餓喔!」
一如往常,劉阿姨在已經點燃油燈的木屋中回頭對著我微笑,也露出一絲憐惜的神情。
「唉喲…沒吃到午餐為什麼不趕快來找阿姨啦… 今天還帶朋友來喔!來,阿姨煮麵給妳們吃。」
只見劉阿姨把破鐵盆燒滾了水,丟了兩把麵進去。我轉頭對站在一旁的嘉瑜說:
「劉阿姨煮的陽春麵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東西!妳一定要吃吃看!」
嘉瑜低頭看著地上,眼框也濕潤著,直到我們把剛煮好的麵條送進口中,她才終於展露笑容。
之後我們三個人留在木屋中聊天,到太陽下山才離開樹林。路途中,我與嘉瑜談笑著,就像今天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
「阿姨的麵真的好好吃喔!到底有加什麼啊?」
「好像只有一些青菜、豬油跟鹽吧…」
「一定有加什麼秘方吧?就跟妳說的一樣好吃呢!」
看來嘉瑜也對陽春麵讚譽有加,而當時天色已晦暗不清,記得小時候的鄉下都是六點多就天黑了。
「如果有秘方的話,我想就是她加了大便吧!」
我一邊笑一邊回答她,鞋子上殘留的狗屎也不那麼臭了。
嘉瑜也笑了,然後我們就各自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。
之後我很少再跟嘉瑜談心了,我並不覺得是記恨於這次的事件,只是之後也不太知道要聊些什麼,我也越來越習慣獨處。
在回家路上我經過校門口被雷劈的那棵大樹遺址,透過路燈,隱約可以看見它還屹立在此,但這極可能只是我的幻想罷了,畢竟它早就死了。
(完,《我們都是末日殘存者》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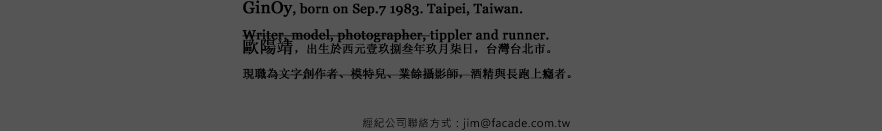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