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叫歐陽靖,生理女性,出生於1983年,七年級草莓族,不太會讀書,但喜歡一些音樂與藝文的東西。我是台灣獨立樂團的樂迷,我沒有在玩團,也沒有在音樂相關產業工作,今天,我想單純以一個粉絲的立場,說一些話,有點長,大家請慢慢聽。
我是在一個開放的教育環境下長大的,小時候家中有一位同父異母、大我12歲的哥哥,記得夏天時他總是躲在房間內,一邊吹著電風扇、一邊翻著《北斗神拳》的盜版漫畫,還用音響播放飛鳥涼的卡帶來聽(不是Chage&Aska,就是飛鳥涼)。可能是受哥哥的喜好影響,我小學五年級時第一次走進唱片行買的卡帶是Mr.Children的專輯,少年時期一直都很投入在J-Rock的世界中。
浦澤直樹的漫畫《20世紀少年》中,當賢知小時候初聽到搖滾樂時,突然覺得整個世界都放大了…不誇張,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腦袋被雷擊的感覺,是在1995年的某個深夜。那晚父母都睡了,我躡手躡腳地走進未開燈的客廳,打開電視轉到第四台,莫名其妙看到” Blankey Jet City”的某支Live PV,頓時,我傻了,我感到五雷轟頂,只能張大眼睛凝望那不停閃爍的映像管顯示器…我心想:「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棒的東西!」。

那一刻,改變了我的一生。
中間的轉折點有點忘了,但不知怎麼搞的?大約國三開始,我就從J-Rock聽到Metal去了。Metallica、Megadeth、NIN、Cradle of Filth…那時的我完全同意『外國的月亮比較圓』這句話。上高中後更是狂聽時下最流行的Nu Metal,Korn、System of a Down…熱音社練的還是Slipknot。
「我要當一個Rocker!」當時的我擁有這麼天真、這麼熱血的想法。我買了Bass、買了音箱,練到手指長繭(第一首練的歌是Blur的Song 2,因為最簡單)。我還在右手虎口位置刺了一個”Anarchy”圖案,只因為那樣彈Bass看起來比較帥,況且我也突然沉迷於Punk Rock Music,那時好喜歡Anti-Flag、Rancid、Misfits…至於The Clash跟Dead Kennedys對我來說根本就是神明一樣的存在,他們的音樂是聖樂。

那時開始跑聖界、跑地社,後來因為野台的關係認識了廢人幫,更常跑台中阿拉。第一次自己坐統聯下台中,一走出火車站就看到一個留著彩色龐克頭的人(應該是小鑫),「台中真的是台灣龐克之都啊~」我在心中持續讚嘆,並默默感動著。無政府、神經、濁水溪…看到他們的表演現場,我的感動甚至比當初聽國外樂團還深…我期許自己將來要像他們一樣,我要玩團!
………也不算多意外的是,『玩團』這夢想,很快就止步了。
高三那一年,我鼓起勇氣決定告訴媽媽自己想當個樂手這件事,當時的心情簡直比出櫃還緊張。我們家一直都是開放教育,我也在心中隱隱預設媽媽會支持的立場;而我媽卻只對我說了一句話:「不行,我沒有錢給妳玩樂團。」她的態度異常堅定。脆弱的我,居然就此放棄。媽媽也曾強力反對我玩攝影,但我還是瞞著她去沖印店打工、買相機,堅持理想至今;兩相比較之下,很明顯就能發現,我在於玩團這理想面的懦弱...
我對於說出『想成為一個Rocker』的自己感到好羞愧。
往後,我開始聽post rock或是一些更深刻的東西,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、Diamanda Galás、PJ Harvey、Nick Drake…反正當時的自己好像在找尋迷失的靈魂一樣,什麼音樂都聽。這些音頻激勵了我的創作,它完整了我。

音樂不只是靈魂的聲音,音樂還能改變這個世界。Jimi Hendrix、Bob Marley、Sex Pistols、Patti Smith…他們都曾經是獨立樂手(樂團),而他們藉著一次次的表演機會,進而改變了這個世界。

我不是音樂人,但是個不專業的小樂迷,剛開始去地下社會,看到666、看到1976、看到骨肉皮…其實我緊張得要死,卻還是強裝鎮定開心地與他們一同乾杯。台灣獨立團的程度高到很可怕,有些獨立團在國外的知名度還高過在台灣內,國際音樂祭活動更是紛紛爭相邀請表演。在這圈子我逐漸了解到:樂團不是用”玩”的,而是要好好經營,經營創作、經營友情。除非你跟《重金屬叔要成名(Anvil! The Story of Anvil)》一樣熱血,不然光靠著一股熱血與衝動是撐不了多久的…這樣說也有點不合邏輯,因為咱們台灣的獨立音樂人,大都過著『白天上班、晚上玩團』的生活,辛苦工作只為了在現實面能支撐自己的理想,這何嘗不是一股熱血?(笑)
我以身為台灣人為傲。台灣很好,24小時都有高CP值的美食可吃,人民性格溫潤、重人情,沒有大山大水,卻有蒼鬱險峻的中央山脈與湛藍的花東海岸線;農產富饒、老百姓熱心公益,但以上並不足引以『為傲』…真正會讓我打從心裡覺得:「身為一個台灣人好屌」的東西,是台灣蓬勃發展的藝文產業。雲門舞集、優人神鼓那些有多厲害你一定知道,但你知不知道『創作歌手』與『獨立音樂』也是台灣足以揚名國際的瑰寶?
台灣有如此多的創作人才,在華語流行樂市場顯而易見,而有更多人才選擇做一個不向商業結構低頭的獨立音樂人,只因為他們也相信:「音樂能改變這個社會」。
音樂的社會意識不能被金錢與利益所蒙蔽…於是,窮困地在indie圈中打滾十數年、創作出無數佳作卻依然一貧如洗的樂手大有人在。好險當初母親有阻止我玩團,我才了解自己對音樂的熱忱遠遠不及這種程度。
台灣獨立音樂陪伴了我十數年,我一值在這大家庭內。2011年3月,台中阿拉夜店大火,當初廢人幫在那舉行廢趴跟倉庫搖滾的Live house阿拉,在數年前已默默轉型為有鋼管舞者、猛男表演的酒吧。
你們知道嗎?在台灣的法條之中,『Live house』是根本不存在的,因為有販賣酒精飲料的營業性質,造成台灣法條將『Live house』歸類為跟林森北路的酒店、Piano Bar是一樣的東西。但Live house辦獨立樂團表演、賣門票,賣掉幾瓶啤酒能賺多少錢?卻得跟獲利相差甚遠的酒店一樣,向政府買同樣昂貴的八大『酒牌』。

阿拉當然要轉型經營,它不轉型,怎麼活得下去?政府口口聲聲說支持文創,甚至撥出輔導金款項讓獨立樂團申請,卻不讓樂團的表演空間有個得以『正名』的生存保障。『Live house』的特殊營業性質本來就應該獨立出來,這是在好久好久之前就該修法的東西,直至今日,地下社會已經宣告不治,我們的法令卻還是跟數十年前一樣。
有人說獨立音樂是『次文化』,本來就不被政府官員所關注,但『文化』這兩個字的定義到底是什麼?什麼是『主流文化』?什麼是『次文化』?什麼樣的人叫做『有文化』?
對許多人來說,『有文化的人』,就是居住在師大之類的文教區附近,媽媽參加社區讀書會,小孩放學後去上才藝補習班…爸爸坐台灣大車隊計程車上班時還會順便聽到愛樂交響電台。對他們而言,這些『玩樂團的』,喝酒、刺青、在陰影下對社會不公平面發出巨大的怒吼與反動;這些不良少年,超沒有文化的。
農村武裝青年、濁水溪、閃靈、交工…他們對體制直接宣戰;1976、甜梅號、瓢蟲…他們帶我們由私領域自省與體制對決。台灣獨立樂團什麼類型都有,Metal、Punk、SKA、Post-Rock…不但什麼音樂風格都有,最特別的,是幾乎所有樂團成員間都是好朋友、都在同一個大家庭內,擁有同樣的價值觀與社會意識!這對全世界的地下樂團文化來說都算是相當特別的一點。

台灣是海島國家,經過荷蘭、日本、國民政府統治,民主政治體系、宗教自由…台灣比世界上更多國家都有接收『多元文化』的條件。但我們的政府卻在使用近似共產黨的手段,把一切『樣板化』、『和諧化』。文林苑都更案王家被強拆,政府說是『依法行事』,而今日,政府同樣『依法』打壓Live house的生存權、打壓獨立音樂人的表演空間。或許未來,我們的獨立音樂人只能去想辦法申請街頭藝人證,在捷運地下街擺箱子等待路人投錢。
我是台灣獨立樂團的小樂迷,我沒有在玩團,也沒有在音樂相關產業工作,但今天,我單純以一個粉絲的立場,說一些話。
要罵我鄉愿也好,但獨立音樂的確改變了我的一生,要不是獨立音樂,我將不會知道原來可以藉由藝術勇敢表達自己的聲音。音樂可以改變這個社會,甚至改變這個世界;但在此之前,我們必須先去影響那些封閉自我、不願意接受改變的人。
2012/7/4 GinOy 歐陽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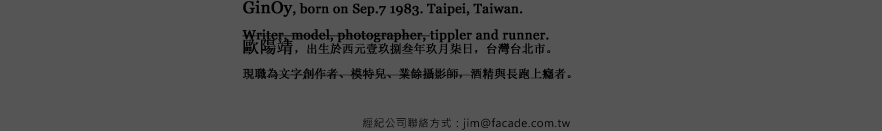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